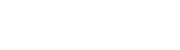坦白父亲侵华往事,村上春树令人尊敬,下面是新京报给大家的分享,一起来看看。
村上春树怎么死的
■ 观察家
近日,日本“国民作家”村上春树在《文艺春秋》杂志上发表文章《弃猫,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》,第一次对外公布了其父亲曾是“侵华日军”,并曾经杀害中国俘虏的残忍往事。
村上春树表示,父亲曾向他断断续续讲过参与侵华战争的经历,这也是他后来与父亲疏远的真正原因,因为他是侵华日军的直系后代,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历史的原罪,他不得不接过父亲的战争记忆。
作为广受中国读者喜欢的作家,村上的坦白让人对他的尊敬更多一分。
据报道,村上春树的父亲叫村上千秋,1938年被征兵到了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16连队当辎重兵。据村上春树回忆,父亲的余生都在佛坛前度过,为死在战场上的人们祈祷。
父亲很少给村上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,唯一讲自己残杀中国战俘的事,是在村上读小学低年级的时候——“显然中国士兵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,但是却没有表现出恐惧和害怕。”村上春树表示,“我的父亲,一直深怀着对中国军人的敬意,恐怕到他死的时候都是如此。”
村上春树不是一个历史作家,但是他也多次呼吁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进行深刻反省,对南京大屠杀进行道歉——他的坦白,也是这种思索的延续。
坦白历史就是承认历史,也是承担责任的第一步。
当然,不管父辈曾有过怎样的罪行,村上春树本人都是没有责任的。1949年1月出生的村上春树,是战后一代的代表人物,成长在和平年代,见证日本社会不断走向繁荣。而他的小说,大多刻画日本都市中人的生活,对中国读者也有很大影响。他写的饮食、音乐,都影响到中国新一代年轻人,很多人甚至追随村上春树跑步,像他一样生活。
换句话说,人们并不期望作为一个日本作家,村上春树必须去思考和反省侵华历史。但也正因如此,村上春树坦白父亲的罪行,才有着某种深刻的意义。
他在文章中写道:“我们只是落向广袤大地的众多雨滴中那无名的一滴。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历史,也有继承那段往事的责任。”村上春树的意思再明白不过:每一个人,都应该承担属于他的那一份责任,否则所谓历史责任也就没有意义。
二战后对日军战犯的审讯,曾让负责案件的美国法官们非常困惑。即便是南京大屠杀时负责上海战区的将军,也都一脸无辜,只把自己当成一个执行上面任务的人。对此,伊恩·布鲁玛的《创造日本:1853-1964》一书有着精彩的分析:由于日本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“摆脱责任机制”,每个高级战俘,都一脸真诚地相信自己的无辜。
“雪崩时,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”,但责任扩散效应很容易让有些“雪花”认为,自己就是无辜的。而村上春树却抛出了另一种内含反思性的历史观:就算只是雨水中的一滴,只是暴雪中的一片,也有承担历史的责任。
当下,当我们说起历史责任时,往往也指那种整体性的责任。该为这种整体性责任负责的,也是能代表官方立场的属“公”组织。但历史也是具体而微的。现实更让人动容的,是具体的、鲜活的人能够站出来,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。
唯有反思,唯有承担责任,才能让人性抵达离善更近的地方。不光是侵华战争,一切历史灾难都是如此。只有具体的人,具体的道歉,具体的忏悔以及具体的惩罚、原谅与宽恕,才更有力量。
□张丰(媒体人)
村上春树啥意思
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小说家——至少在我29岁前从未这么想过。这是千真万确的。
我自小便喜欢阅读,喜欢将自己沉浸于小说的广袤世界中,要说我不想写些什么,那是假的。可我从不认为自己有写故事的天赋。青年时代的我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,卡夫卡和巴尔扎克,但却从未想过自己能有资格与他们并肩。正因如此,我很早就打消了自己写小说的念头。阅读将作为爱好而继续,我还得另谋糊口的出路。
我最终落脚的领域是音乐。我刻苦工作,努力攒钱,又四处奔走借了一些,大学毕业不久后在东京开了一个小小的爵士俱乐部,日间卖咖啡,晚上供酒,也能做些简单的食物。唱片声时时萦绕耳畔,周末会有年轻乐手来作爵士乐现场演出。如是过了七年。所因为何?很简单——我能从早到晚都沉醉于爵士乐中。
15岁我与爵士乐初相识,那是1964年。Art Blakey和Jazz Messengers乐队一月在神户公开演出,而我有幸得到一张入场券作为生日礼物。这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地聆听爵士乐,它让我为之震颤。Art Blakey厚重而富于想象的鼓点声引导下的Wayne Shorter的中音萨克斯,配上Freddie Hubbard的小号和Curtis Fuller的长号,这一阵容在爵士乐历史上都算是数一数二的了。我从未听过如此迷人的音乐,无法自拔。
一年前,我在波士顿与巴拿马爵士钢琴家Danilo Pérez共进晚餐时告诉了他我的童年经历。他当即拿出手机问我:“村上,想和Wayne聊聊吗?”“乐意至极。”我答道,事实上我已经激动到词穷了。他拨通了远在佛罗里达的Wayne Shorter并把手机递给我。我对WayneShorter说,无论在那之前还是自那以后,我都没有再听到过如此美妙的音乐了。生活如此奇妙,你永远无从预测。42年后的今天,我写着小说,定居波士顿,在手机里和Wayne Shorter聊天…这是我从未料想到的。
29岁那年,写小说的念头忽然击中了我——而我也确实能够做到。诚然,我写不出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巴尔扎克相提并论的作品,但我安慰自己这没关系,我无意成为一名大文豪。即便如此,我依旧毫无头绪,不知写些什么,又从何写起。作为新手,我没有什么既定的风格,没有可供请教的前辈,甚至也没有能探讨一番的朋友,只是想着,若是能像弹奏乐器一样写作的话,大约会是桩很美妙的体验。
我自幼练习钢琴,也到了能从大段乐章中抓抄下某个简单旋律的程度,可我还没有那种成为职业音乐家所需的火候。虽然在内心深处,我总能听到某种像是我自己的音乐以汹涌澎湃之势盘旋而至。我思忖着这种音乐是否能经由笔尖流淌出来,而我的风格也就是这样起家的。
不论是在音乐还是小说中,最基本的要素便是节奏。风格本身依托良好的、自然的、平稳的节奏而得以呈现,否则没有人会想继续读下去。音乐——尤其爵士乐教会了我节奏的重要性。接下来便是旋律——从文学角度来说,就是将词语适当安排,从而与节奏相契合。如果词语能以一种平滑而适宜的方式嵌入节奏中,那便别无他求了。再其次是和声——承载词语的内在精神共鸣。然后是我的最爱:即兴演奏。藉由特定渠道,故事由内而外自由流淌,我只要跟着感觉潜入这股律动中去即可。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部分——在结束“演奏”之余,觉着自己到达了一处全新的意义非凡的所在。如果一切进展顺利,你或许能将那种飞升感与读者共享。要达到这一高潮并无其他途径。
几乎我所知道的关于写作的一切都源于我对音乐的认识。说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,可若是没有我对音乐的痴迷,我大约不会成为一个小说家。即使是整整30年后的今天,我依旧从好的音乐中汲取写作的技巧。就像F.Scott Fitzgerald优雅如行云流水般的散文深受Charlie Parker的即兴重复影响一样,我也借鉴了Miles Davis音乐中不断的自我更新,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学模式。
一直以来,Thelonious Monk都是我非常喜爱的爵士钢琴家。一次当被问起他是如何使钢琴发出那种特殊声响的,他指了指琴键,回答道:“没有一个琴键是新的,你看,它们早已被安妥在那儿,唯有对其注入重视,方能令其越众而出。”“唯有对其注入重视啊。”他这样说。
我在写作时常回想起这句话,并喃喃自语道:“诚然,日光之下并无新词,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寻常词汇赋予崭新的含义和弦外之音。”这一想法使我感到安心。即是说,广袤的未知依旧铺陈于我们眼前,而所有界限只是常规,等待被超越。